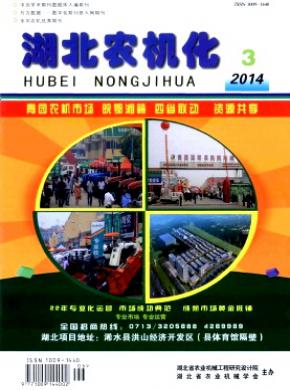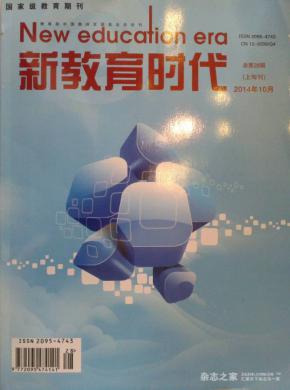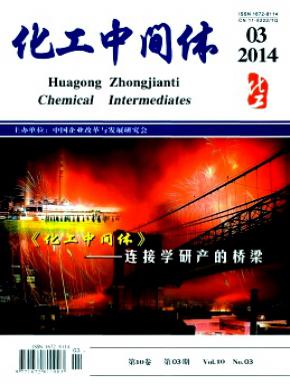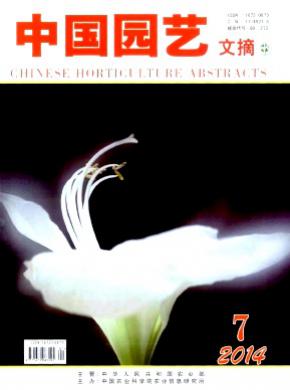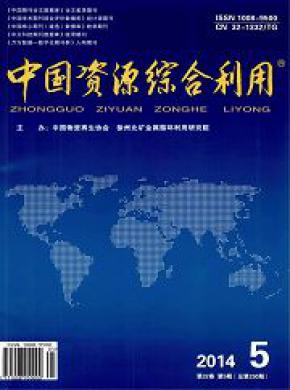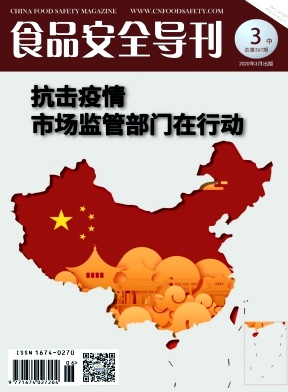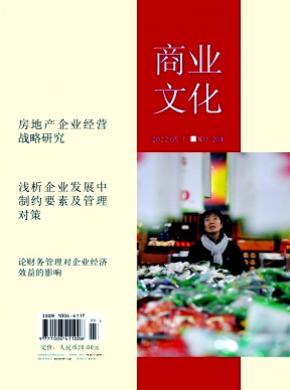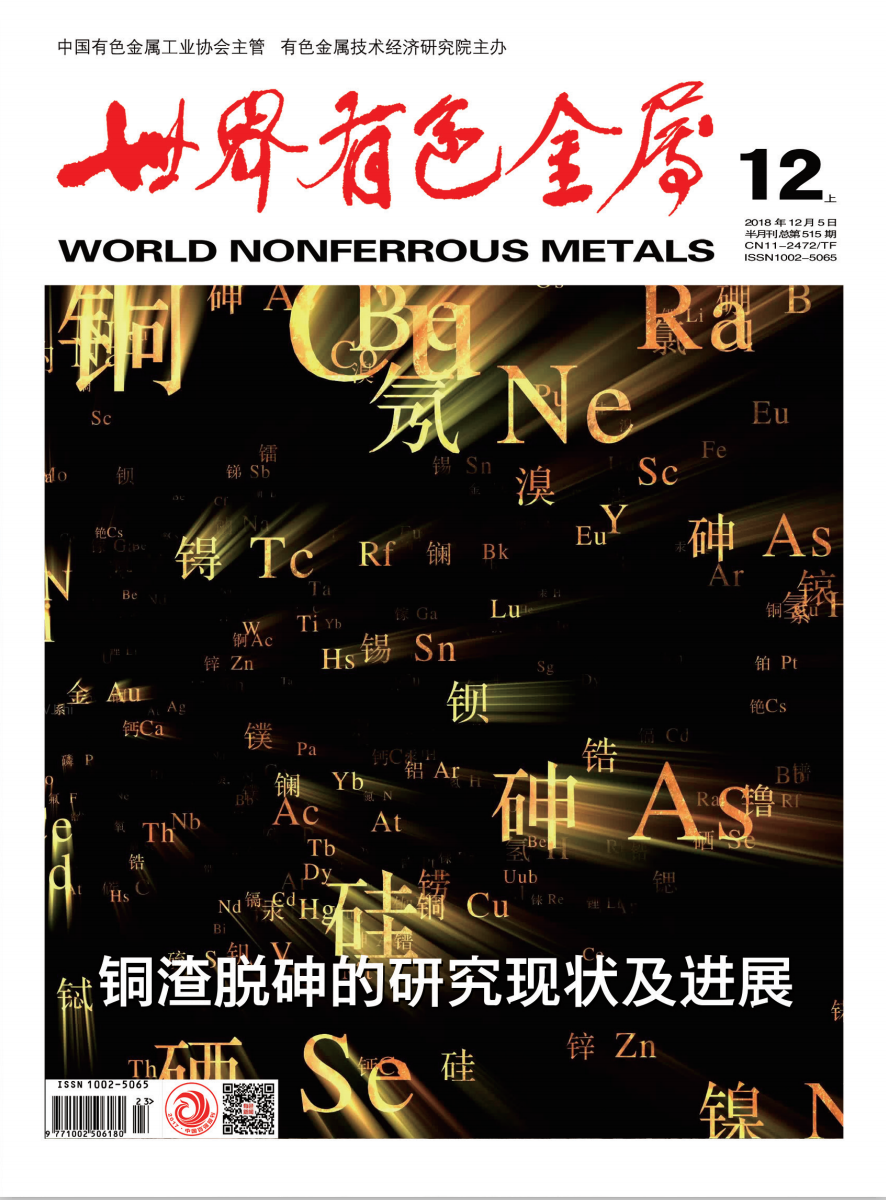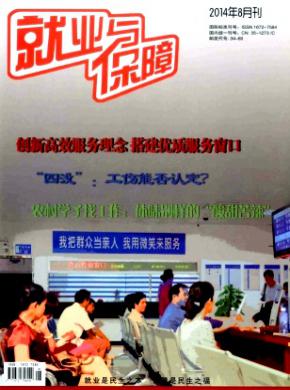科学家在量子物理学出现前一个世纪将光与物质联系起来
爱尔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威廉·罗文·汉密尔顿 (William Rowan Hamilton) 出生于 220 年前的上个月,他以雕刻一些数学涂鸦1843 年进入都柏林的布鲁姆桥。
但在他的一生中,汉密尔顿的声誉取决于 1820 年代和 1830 年代初所做的工作,当时他还只有 20 多岁。他开发了新的数学工具来研究光线(或“几何光学”)和物体运动(“力学”)。
有趣的是,汉密尔顿使用光线路径和材料粒子路径之间的类比来发展了他的力学。
如果光是物质粒子,正如艾萨克·牛顿所相信的那样,这并不奇怪,但如果它是波呢?波和粒子方程在某种程度上相似意味着什么?
一个世纪后,当量子力学的先驱们意识到汉密尔顿的方法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类比:它只是对物理世界真实本质的一瞥。
光的谜题
要理解汉密尔顿在这个故事中的地位,我们需要再往前追溯一点。对于普通物体或粒子,牛顿于 1687 年发表了运动的基本定律(或方程)。在接下来的 150 年里,伦纳德·欧拉、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和汉密尔顿等研究人员对牛顿的思想提出了更灵活、更复杂的版本。
“汉密顿力学”被证明非常有用,以至于直到 1925 年——将近 100 年后——才有人停下来重新审视汉密尔顿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无论光的真实性质如何,他对光路的类比都有效,但在当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光是一种波。
1801年,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进行了他著名的双缝实验,其中两束光束产生了一种“干涉”图案,就像当两块石头扔进去时池塘上重叠的涟漪一样。六十年后,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意识到光在电磁场中的行为就像涟漪波。
但随后,在 1905 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表明,只有当光也可以表现为类似粒子的“光子”流(后来被称为光子)时,才能解释光的一些特性。他将这个想法与马克斯·普朗克 (Max Planck) 在 1900 年提出的一项建议联系起来,即原子只能以离散的团块形式发射或吸收能量。
能量、频率和质量
在他 1905 年关于光电效应的论文中,光将电子从某些金属中移走,爱因斯坦使用了普朗克公式来表示这些能量块(或量子):E = hν。E 是能量,ν(希腊字母 nu)是光子的频率,h 是一个称为普朗克常数的数字。
但在同年的另一篇论文中,爱因斯坦引入了一种不同的粒子能量公式:现在著名的 E = mc ² 的一个版本。E 又是能量,m 是粒子的质量,c 是光速。
因此,这里有两种计算能量的方法:一种与光相关,取决于光的频率(与振荡或波相关的量);另一个与材料颗粒相关,取决于质量。
1924 年,路易斯·德布罗意 (Louis de Broglie) 发现了这条线索,他提出物质就像光一样,既可以表现为波,也可以表现为粒子。随后的实验证明他是对的,但很明显,电子和质子等量子粒子的规则与日常物体截然不同。
需要一种新的力学:“量子力学”。
波动方程
1925 年迎来了两种新理论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首先是“矩阵力学”,由维尔纳·海森堡发起,马克斯·玻恩、保罗·狄拉克等人发展。
几个月后,欧文·薛定谔开始研究“波浪力学”。这让我们回到汉密尔顿。
薛定谔对汉密尔顿在光学和力学之间的类比感到震惊。凭借想象力的飞跃和深思熟虑,他能够将德布罗意的想法和汉密尔顿的物质粒子方程结合起来,为粒子产生一个“波动方程”。
一个普通的波动方程显示了“波动函数”如何随时间和空间变化。例如,对于声波,波动方程显示了空气在不同位置随时间变化的压力变化而发生的位移。
但根据薛定谔的波函数,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在波动。事实上,它是否代表物理波或仅仅是一种数学上的便利仍然存在争议。
波浪和粒子
尽管如此,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学的核心,它支撑着我们许多现代技术——从计算机芯片到激光和光纤通信,从太阳能电池到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电子显微镜、GPS 中使用的原子钟等等。
事实上,无论是什么在挥动,薛定谔方程都可用于准确预测在给定时间和地点观察到粒子(例如原子中的电子)的机会。
这是量子世界的另一个奇怪之处:它是概率性的,所以你无法像“经典”物理学方程对板球和通信卫星等日常粒子所做的那样,提前将这些不断振荡的电子固定到一个确定的位置。
薛定谔的波动方程首次能够正确分析只有一个电子的氢原子。特别是,它解释了为什么原子的电子只能占据特定的(量子化)能级。
最终表明,薛定谔的量子波和海森堡的量子矩阵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等价的。海森堡也使用汉密顿力学作为指导。
今天,量子方程仍然经常根据其总能量来编写——这个量称为“哈密顿量”,基于汉密尔顿对机械系统能量的表达式。
汉密尔顿曾希望他通过类比光线开发的力学能够被证明是广泛适用的。但他肯定从未想过他的类比在我们理解量子世界时会有多么有先见之明。